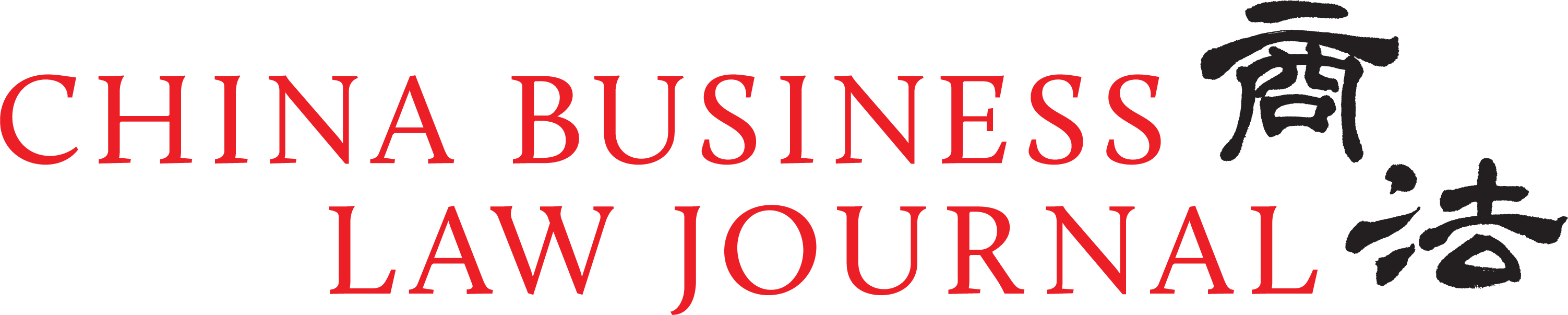问题一:赴港上市企业可能面临哪些跨境争议与合规问题?
截止2024年底,根据港交所的分类,内地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478家,其中364家为H股,其余1114家为非H股(也就包括红筹架构和VIE架构)。而到今年,截止9月19日已在中国证监会备案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达60家,在数量上几乎与今年同期A股IPO的企业上市平齐。可见,在境内IPO机会受限的情况下,香港已经成为境内企业上市的重要选择。
赴港上市企业面临自身情况的双重变化,一是从非上市公司变成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需要面对资本市场对其公开性、公平性的要求和监督,对公众股东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义务将成为赴港上市企业的全新课题;二是从境内企业变成跨境企业,跨法域这个问题会对公司的业务、财务、税务、外汇等也造成全方位的影响,不同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定在前期合规运作及后期争议处理上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同时,由于我们面临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这种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在不断变化,并且通过事后爆发的各种争议和问题给后来者以启示。此次分论坛,我们希望探讨的就是结合已有的跨境争议与合规经验,对于拟赴港上市的企业或者还未碰到此类问题的港交所上市企业能有一些启示。
问题二:香港作为特殊的境外法域,在争议解决方面有哪些特殊的规则?
一旦发生涉港的争议,那么对于争议如何解决就要涉及两方面的视角,首先香港是境外法域,属于普通法法系,在争议处理程序与实体裁判观点上均可能与境内不同;其次香港是我国的一部分,相比其他法域,香港与内地在司法协同性上具有独特优势。
例如,在仲裁裁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方面,在2000年颁布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在2020年颁布了《补充安排》,为两地仲裁裁决在对方法院申请执行提供了细致的规则依据。同时,基于《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在仲裁裁决作出前,当事人可向对方法院申请财产、证据、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极大加强了中间措施的力度,能够保护当事人在申请仲裁至仲裁裁决作出之间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供了通过中间措施减轻诉累的可能。
在民商事判决的相互认可和执行方面,以2024年1月29日起施行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为标志,除了八类明确列示的民商事案件以外,双方司法判决的认可与执行覆盖大多数民商事案件,并对平行诉讼导致冲突的不予认可和执行进行了规定。此前两地还单独签订有关于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及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为诉讼程序中的司法协助提供了可行性和便利性。
今年2月,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基于广东高院的请示,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登记设立的香港、澳门投资企业协议选择港澳法律为合同适用法律或者协议选定港澳为仲裁地效力问题的批复》,认可在深圳市、珠海市登记设立的港澳投资企业约定适用港澳地区法律,以及在内地九市登记设立的港澳投资企业约定以港澳为仲裁地的仲裁协议效力,推进“港资港法港仲裁”,优化营商环境。
这些都是涉港争议的特殊规则,并且一直在不断优化演进。
问题三:赴港上市企业面临怎样的资本市场合规监管挑战?
《证券法》在19年修订时将其适用范围向“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进行了扩大到,根据第二条第4款的规定,“在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证券法》有关规定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对于赴港上市企业来说,特别是“A+H”的上市模式下,在境外披露的信息也需要在境内同时披露,若在港股发生信息披露违法事件对A股将产生明确的传导影响。进一步的,在中国证监会2023年2月发布《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及5项配套指引后,以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也基于备案要求,被统一纳入中国证监会的监管视野。
特别的,近年来还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引发的虚假陈述股民诉讼案件,并且出现了多起境内投资者对在境外资本市场出现信息披露问题的中国企业向境内法院提起证券欺诈诉讼的案件。北京金融法院于今年4月首次裁定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在港上市境外公司证券欺诈诉讼具有管辖权,并经北京高院维持裁定。法院认为,关于证券法域外效力的适用条件“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与“损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两种情形并非需要同时满足,满足其一就可以触发域外管辖。赴港上市企业面临着内地和香港两地的资本市场合规监管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