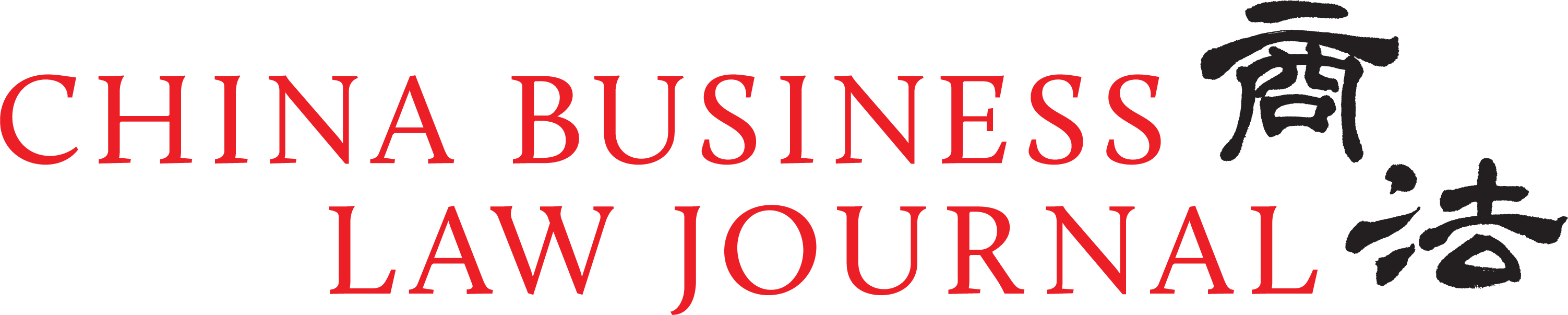28 Nov 2025
15:35 - 16:35
分会场三
痛点一:多方参与下的责任界定与风险分配极其复杂 (Liability Demarcation and Risk Allocation)
可信数据空间(TDS)本质上是一个多方协作的生态系统,参与方包括数据提供方(如医院)、数据使用方(如药企、科研机构)、技术平台方(TDS建设和运营方)、以及数据主体(患者)。在这种“多对多”的网状结构中,传统的“一对一”或线性的法律责任关系被打破,产生了复杂的权责难题。
核心关注点:
- 责任的“黑盒”:当发生数据泄露、滥用或因数据分析结果错误导致损害时,如何精准定位责任方?是提供原始数据的医院数据质量有问题?是使用方在分析过程中超出了授权范围?还是TDS平台本身存在技术漏洞或安全缺陷?在技术高度复杂的“数据沙箱”或“联邦计算”环境中,举证和溯源的难度极大。
- 合同的“蛛网”:如何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合同框架来厘清各方权责利?这需要起草和审阅大量跨主体协议,如数据提供协议、平台服务协议、数据使用/授权协议等。这些协议必须无缝衔接,清晰界定数据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和处理者(Data Processor)的角色,并明确约定在各种潜在风险场景下的责任承担比例、赔偿上限以及追索机制。这对合同的精细化和前瞻性提出了极高要求。
- 风险的“传导”:生态中任何一方的合规短板都可能成为整个TDS的“阿喀琉斯之踵”。例如,一家参与医院的内部数据治理不善,可能导致整个数据空间的数据质量受损或面临合规风险。法务需要评估和管理这种系统性的传导风险。
简言之,痛点在于:在法律责任被技术和复杂的商业模式模糊化的新场景下,如何通过合同设计和治理规则,建立一个清晰、公平且可执行的责任分配体系,以保护我方(无论是哪一方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痛点二:现有法律框架的适用性与新模式的内在冲突 (Applicability of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s)
TDS的核心理念是“数据价值流动,而非原始数据流动”,这与我国现行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为核心的法律框架在某些方面存在张力。现有法律大多是基于“告知-同意”、“目的限制”和“最小必要”等传统数据处理原则构建的。
核心关注点:
- “告知-同意”原则的挑战:在TDS模式下,医疗数据的用途可能是动态和探索性的,难以在数据收集之初就向患者(数据主体)进行全面、详尽的告知。如何获取一个既合法合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未来研究需求的“概括性同意”或“动态授权”,是一个巨大的合规难题。过于宽泛的同意可能被认定为无效,而过于狭窄的同意则会扼杀TDS的价值。
- “目的限制”与“最小必要”原则的再解释:TDS鼓励数据的二次、多次开发利用以释放价值。这是否会与个人信息处理的“目的限制”原则相冲突?在“可用不可见”的技术保护下,如何向监管机构证明数据处理活动始终遵循了“最小必要”原则?比如,一个AI模型训练项目,法务需要审慎评估其使用的数据范围是否超出了实现该模型训练目的所必需的最小范围。
- 匿名化的认定标准:TDS常常依赖去标识化或匿名化技术。然而,根据法律规定,匿名化的标准是“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在医疗数据这种高敏感、高维度的场景下,多维度数据聚合后,是否存在“再识别”的风险?技术上声称的“匿名化”是否能得到司法和监管的最终认可,存在不确定性。
简言之,痛点在于:如何在拥抱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整个业务模式能够严谨地嵌入现有的法律监管框架内,避免因法律适用性的争议而引发颠覆性的合规风险。这要求法务不仅要理解法律条文,更要深刻理解技术逻辑。
痛点三:数据资产的权属与价值分配的法律难题 (Legal Issues of Data Asset Ownership and Value Distribution)
当医疗数据在TDS中被加工、分析、建模并产生巨大商业或社会价值时,一个核心的法律问题浮出水面:这些衍生的数据产品或洞见(Insight)的“所有权”或相关权益归谁所有?其产生的收益应如何在各参与方之间进行公平分配?
核心关注点:
- 数据资产的定性:在法律上,原始医疗数据、经过去标识化处理的数据、以及最终形成的分析模型或研究报告,它们的法律性质和权属归属是什么?目前法律对此尚无明确界定,这为商业谈判和纠纷解决埋下了隐患。
- 价值分配的依据:如何设计一个公平、透明的价值分配模型?是按提供数据的数量、质量,还是按数据在特定应用场景中的贡献度来计算?这需要法务与业务、技术团队紧密合作,将商业逻辑转化为严谨的、可量化的合同条款,以避免未来的履约争议。